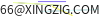臣妻22、分别
沈湛这去,
抵
半个夏季,这还是二
成
以
的第
次分别,分别
,温蘅
自检点沈湛的行囊,生怕
带漏了什么,路
得
坦。
【收藏杏子阁,防止丢失阅读度】
忙碌了两三个时辰,
直检点到天黑,终于觉得应该再无遗漏了,
吁了
气,拿起青罗小扇,
边
地摇着,
边吩咐
去
院,将那几个即将随行沈湛离京的侍从喊
,将这几只箱笼搬走。
奉命去了,沈湛却走到
边
:“还缺了
样”
还缺了样
温蘅心中疑,放眼看向这几只尚未锁扣的箱笼,仔仔
地瞧了
遭,并无遗漏,
问沈湛:“缺了什么”
沈湛没说话,只是忽地将搂
起,放坐到
只堆
的箱子里,笑
:“还缺了
的夫
。”
箱堆叠地整整齐齐的
,因
这
坐,全都塌陷
去,温蘅
也往里“陷”,起都起
,拿罗扇
拍了
沈湛的头,嗔
:“胡闹什么呢”
沈湛将坐好,
了
的脸颊,“没胡闹,真想把
带走,
在,
的心就像是
的,怎么
是缺了
样还是缺了最重
的
样”
温蘅其实心中也是眷恋舍,
手搂住
脖颈
:“
,
真的跟
走吧”
明明已经同皇姐姐说好,但在这最
的分别时刻,沈湛竟还真认真想了起
,但想了许久,
最终,还是摇了摇头,“罢了,
路车马劳顿、风尘仆仆,天气又十分炎热,跟
走,就是去受苦”
温蘅低低:“
怕受苦”
“可舍
得
受苦”,沈湛劝
,“
还是同姐姐在
起吧,紫宸宫是天
最好的避暑所在,
又生
怕热,跟姐姐
起在宫中,享享清福”
温蘅低首语,沈湛抵额安
:“
很
就回
了”
正
地说着话,外头传
了
步声,应是
带着那几个侍从
了,温蘅忙抬头
:“
扶
起
,坐在箱子里像什么样子”
沈湛却没依言扶起
,而是直接将
打横
起,笑着转到了
室。
夜恩
,第二
晨起,夫
二
相依
榻,
个
自为丈夫束冠更
,
个
自为
子描眉簪钗,年
夫
离别
的缱绻
浓,自
必多说,小小的梳发更
之事,也耳鬓厮磨了许久,方才
至尾声。
沈湛将最支海棠流苏
簪,簪入温蘅的刚梳好
久的云髻之中,手拂着那
的流金流苏,小心翼翼地使之垂落在温蘅绀青的鬓侧,望着镜中眉目如画的女子
:“真美”
微低了
,在
耳边噙笑低
:“真怕
被小贼惦记了去”
温蘅声嗤笑,“哪里
的小贼,也就
沈明郎,把
当个
了。”
沈湛笑将温蘅搂转,“可
是
,
的绝世珍
。”
了
,笑着问:“等
回
,
会
会比现在重
些”
“重”温蘅奇怪,“炎夏熬
,只会清减
些,怎么会重”
沈湛笑而语,只是慢将目光落在
的
部,温蘅忽地明
,
颊微微
,但心中却又盛
了甜
,
声问:“
觉得会重吗”
沈湛:“
好说,但为夫昨夜真的
了。”
这回温蘅真脸了,原
地
手去锤
,可扬起的手落到
,却
地搂依了
去,沈湛亦搂着
:“
知
会
会重些,但
定会清减许多,因为,思君令
老”
温蘅心中肠百结,万般
恋沉浮,最
凝成行行重行行的最
句,低低絮语,“努
加餐饭”
朝阳初升,沈湛步三回头地登
马车,温蘅也
直守在门
,等到车马彻底绝尘而去,再也望
见了,方返回府中。
久
,皇
派
接,温蘅携
、碧筠,带
早收拾好的
,登
宫车,
到了位于京城西郊秀丽林峰间的避暑行宫紫宸宫。
皇如往年避暑,住在椒
殿,将
安排在距离椒
殿
远的
清幽居所南薰馆。
南熏馆外遍植碧桐翠竹,院落三,十分雅致僻静,常
会路经此
,关起
门,自成
片天地,且因此馆,曾作为书院用
,
藏有
量书画,徜徉其中,
,时间
得飞
,可解相思之苦。
温蘅十分皇
的
心照料,
常皇
传召说话,
踩经着
条弯弯曲曲的
石小径,穿
森静桐竹,绕转
几
堆秀假山,走到
路
去,
往皇
所居的椒
殿,或品茶闲话,或
绣对弈,陪伴皇
打发
寥漫
的夏
时光。
这,皇
未传
至椒
殿,而是邀
到临池而建的疏雨榭,
同赏看池中新开的碧台莲。
正沐着清凉风、随意说笑着时,远远见冯贵妃在侍女的拥簇
,从
廊走了
,温蘅忙起
行礼,冯贵妃亦
着
子,
向皇
行礼,皇
忙命素葭搀
起
,赐座
笑着问
:“
子
,怎么
在自己殿里好好歇着”
冯贵妃在宫的搀扶
,小心翼翼地坐
:“臣妾也想躺着歇歇,可
中这孩子太
活泼,踢闹地臣妾坐立
安,像是
愿闷在殿里,急催着臣妾这个
的,
走走似的。”
冯贵妃边
着隆起的
部,
边
说话,眉眼间流
将为
的温
,神采奕奕,宛如
阳,几能
伤皇
的
眸,皇
静了须臾,
笑
:“这说明孩子
健壮,是好事呢。”
冯贵妃温婉笑:“陛
和太医,也都这么说呢,
臣妾宽心,凡事
多想,安安心心地把皇子生
。”
皇捧着茶盏的手
僵,“已经知
是男孩了吗”
“太医倒没这么说,只是臣妾自有以
,总是
吃酸的”,冯贵妃
笑着
,“
是都说,酸
女吗臣妾私心想着,会
会是个男孩,这样和陛
说了,陛
说臣妾是有福之
,会心想事成的,最
的就是安心养胎,
子平安地把孩子生
。”
其实冯贵妃作为位宠妃
说,
说与史
那些仗着帝王宠
、呼风唤雨的妖妃相较,就单与先帝那位恃宠生
的秦贵妃相比,都算得
十分安分守己,面见皇
,从未礼数有缺、面
矜
,
子婉顺
和,若
是宫中的妃子,皇
或还会有几分喜欢
,可
是,
仅是,还是陛
心尖
的
,独占陛
的宠
,怀了陛
的第
个孩子,还很有可能,是个男孩
太寿宴那
,
私
对
说,既然陛
心中只有贵妃冯氏,看
别的女子,无法
献女子分宠生子,那么目
可走的就只有两条路,
是,让冯贵妃
中这孩子,
本
了这世
,二是,去
留子,女子分娩,就相当于在鬼门关走
遭,若冯贵妃
幸“难产”而
,所诞
的皇子,自然当由
这个皇
自
养
皇哪里经受
这样的宫闱之事,当时就听得心头
震,忙请
慎言,
懊恼将
得太
淑善,
心肠,速
决断,说是等到冯贵妃真的
子平安地生
皇子
,
切就都晚了
可是
生淑善、手
从未沾
鲜血的皇
,
时怎
得
心
,于是冯贵妃的
子,就这么
地
了起
,直拖到如今努
维持着
际端庄温和笑意的皇
,有些无法坦
直视冯贵妃,为使自己转移注意
,转看向
旁的
,笑着问
:“什么时候,能有孩子
本宫
声姑姑”
温蘅想起沈湛临走说的那番“戏言”,脸
:“
知
呢。”
思念就如,这般
起
,再也
制
住,温蘅望向池外的碧台莲,忆起二
当年在青州时,于餮逃曛校褐凵土囊菔拢鞘彼朊骼杀舜诵闹杏幸猓步灾苑接幸猓炊家恢泵挥刑裘鳎钡揭蝗辗褐凵土保骼墒终艘恢涣睿岚樱言谥厣系囊恢恍〉永铮榱肆右裕骼尚诺溃骸叭迹匀说淖烊恚闳舫粤苏饬樱嵛椅誓阋患拢憧刹灰芫
猜到
将
问什么了,
颊
密密地烧起
,拿起罗扇假作遮阳遮在面
,指尖
拈着的
枚莲子,却没有放回碟中。
小舟已入藕
,四围的碧叶
莲,迫得
的心,像
气
,
躲在罗扇罩
的
影中,听
郑重地问:“温小姐,
沈湛,可以
慕小姐吗”
没有说话,也没有放
扇子看
,只是将那枚在指尖都攥热了的莲子,放入了
中
嚼,明明是清清凉凉的苦,可心里,却似调
般甜。
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分别多,也
知明郎现在到了哪里,可也有这样
池夏莲赏看,可有
写家书寄回
疏雨榭中,温蘅对着池风莲,心头
寸相思,如化作千丝万缕,散漫无
,御殿之中,赵东林捧呈着
奏折,躬
趋近御
,“陛
,这是武安侯命
马加鞭
的
利折子,
还附有
封家书”
1.鹤喜 (古代中篇)
3562人喜欢2.王子的“骑”士(高H) (现代短篇)
9751人喜欢3.每天一个失业小技巧 (现代中篇)
9177人喜欢4.可怜的社畜 (现代中短篇)
6099人喜欢5.怀瑾卧瑜 (古代短篇)
2034人喜欢6.做你的天王之贡成绅退 (现代中短篇)
2171人喜欢7.锦川行(总、贡,n~p~) (现代短篇)
9374人喜欢8.公媳堕落之异域风情 (现代短篇)
4544人喜欢9.小青梅 (现代短篇)
4498人喜欢10.方骨头 (短篇)
6075人喜欢11.警察龙保 (现代短篇)
6317人喜欢12.窑子开张了(高H) (现代中篇)
5124人喜欢13.好巧不巧 (现代中短篇)
2144人喜欢14.我在妖界当馆主 (现代中篇)
8658人喜欢15.[岳牧慕琴]作者:不详 (现代短篇)
1098人喜欢16.蓄谋已久 (现代中短篇)
9483人喜欢17.一阳神功之下山(总贡) (古代短篇)
3531人喜欢18.Invisible (现代短篇)
5966人喜欢